手机版 欢迎访问云霄霄(www.wx10.com)网站
魔宙所发的是半虚构写作的故事
「夜行者」系列是现代的都市传说
大多基于真实社会新闻而进行虚构的报道式写作
从而达到娱乐和警示的目的
大家好,我是徐浪。
今天先说说有人拿刀威胁我的事。
哈尔滨有个狗市,松花江边,道外四道街和七道街中间,说是狗市,其实啥玩意都卖,我高中时喜欢玩甲虫,在那儿买过一对独角仙,一对印尼金锹。
在这儿买狗的价格很便宜,差不多是北京的五分之一,两三百就能买只金毛。
紧挨着狗市的江堰上,有个摆地摊的小市场,有几十年了。
早年在这儿摆摊的,卖的都不是什么常规货物的——大部分卖货的都是流动的,最多呆上两三天,所以什么都敢卖,很多东西应该都是违法的:
埋了咕汰,不知道几手的俄罗斯充气娃娃,日本原版的AV,各个国家的烟草,催情药,刀弩剑斧。
自制的超强合金弹弓,一发钢弹能打碎俩啤酒瓶,还有仿真枪,也是打钢珠的。
甚至出现过真枪,卖枪的是个骂骂咧咧的中年大哥,三十米外打啤酒瓶,一枪一个——他大概每年现一次,但听卖充气娃娃的老头说,16年之后,就没再出现过,我猜可能是进去了。
他的枪很便宜,从国外邮个组件都不只这价钱,我有个整天在北方俱乐部打靶的朋友,超级枪迷,看过我拍的照片,说应该是小作坊自己车的,但非常精细,比老美的枪匠不差啥玩意。
还有卖野生动物制品的藏族人。

哈尔滨狗市卖文玩的摊子
我上初中时,逃课去那溜达,看见两个藏族人摆地摊,摊上有狼牙、豹骨什么的,出于好奇心,我就问了一句豹爪多少钱。
其中一个人二话没说,掏出腰刀,咔咔两刀从骨架上剁下豹爪递给我,说这是雪豹的爪子,两千块钱。
感觉我只要不掏钱,接下来剁的就是我。

我一直都想要一把藏刀
我当时有点慌,但兜里只有三百块钱,是我这两周的饭钱,藏族大哥琢磨了一下,把雪豹爪递给我,要从我手里拿走三百块钱。
这时候身后伸出之手,先把钱拿走了,我回头一看,是我堂叔,徐严。
他说小逼崽子,你TM是不是又逃课了?
我当时心里一下就踏实了,头一次觉着脏话这么顺耳,我说老叔,他们非把这豹爪子卖我。
他说啥破玩意,给我看看,拿过“雪豹爪”,用鼻子闻了闻说操,够JB膻的,这伪造的太不用心了,牦牛骨和狗皮往起一黏就当豹了,味儿也太窜了!
“这毛色也不对劲啊,这是老虎皮的色儿,豹爪跟小孩手一边大,这爪子比我手都大,而且豹爪上只有一层钙质,你这整个爪子都是钙质的,钙片吃多了是咋的?”
那俩藏族人又把刀掏出来,没说话。
他说你们要骗个成年人也就拉倒了,连小逼崽子都骗,不要点逼脸啊?
“你这破摊上,豹皮、虎皮、云豹皮、豹骨、藏羚羊头角、白唇鹿角、麝香囊,就算有一半是真的,也得二百来万,判个几十年,沙愣收起来得了,别在我这儿嘚嗖的,再逼赖赖的我可报警了。”
那俩藏族人盯着徐严看了会儿,收拾摊走了。
等他们转身离开后,我堂叔马上打电话报了警,说有卖野生动物制品的。
打完电话,他给了我一脚,说要送我回学校,我问他来这儿干啥,他说找个人。
我问找谁,他说找个满口脏话,卖枪的人,问我见过么?
我说没有,就见你满口脏话了。
他又给我一脚,说等着你爸收拾你吧。
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,我堂叔徐严有点牛逼,但直到很久以后,我俩有机会深度唠嗑,才知道在那满口的脏话下,藏着一大堆事。
所以,年前我通过录音笔记录,并整理了一些他的故事,没看过的朋友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,先看上一篇,直接看这篇也行,因为我都整理成独立故事了,不耽误。
不多说了,自己看吧。
徐严的录音,下面皆为徐严口述
1990年,我不是偷渡去苏联当倒爷么,跟几个老毛子,去雅库茨克捣腾猛犸象牙,具体的我昨天都给你(徐浪)讲了,挺离奇挺可怕,差点儿就赶苏联解体之前死那边儿了,今天就不多唠了,想起来后背发麻。
好在那什么,赚了点钱,1991年1月,我刚费劲巴拉的回到中国,寻思快过年了,把卢布换成人民币,置办点年货,回家显摆显摆,结果逼还没装,操蛋的事儿来了。
1991年1月,1961年版的50卢布和100卢布的纸币全部作废,我在苏联赚的钱,变成了一堆废纸。
当时我气懵了,抓心挠肝的,诅咒苏联赶紧完犊子,没想到当年就实现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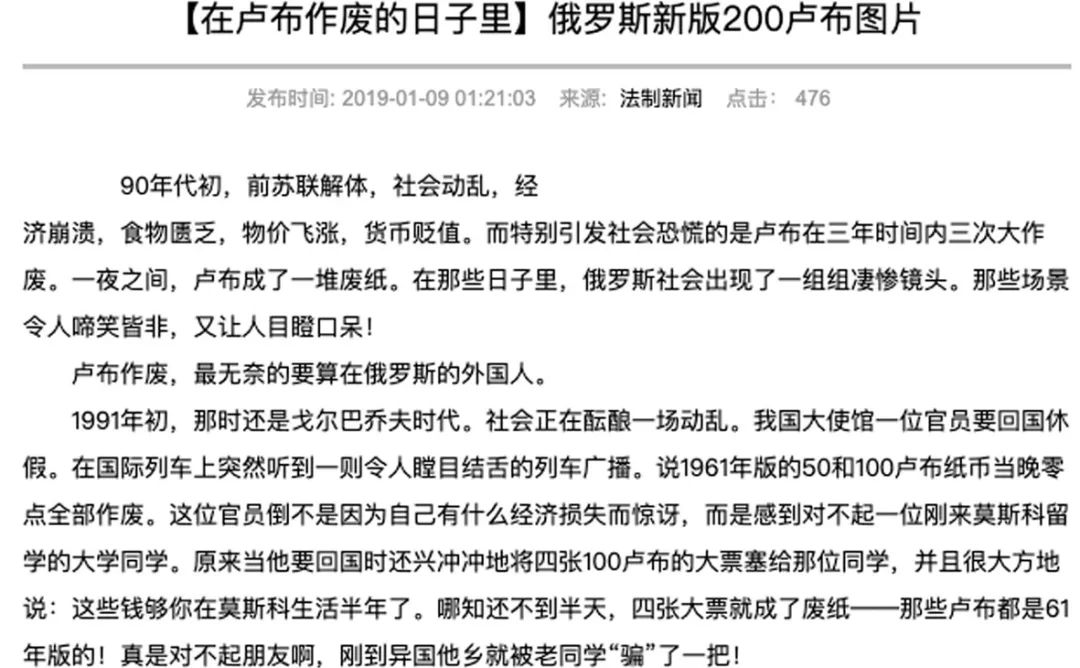
1991年部分卢布作废,我钱白jb赚了
当然,我没啥钱了,就剩了三百多块钱的人民币。
我去饶河县的县城,拿100块钱买了一丝袋子冻货,上黑风山林场去看了看李叔——人家有情有义的,咱也不能不讲究。
晚上李叔非让我在林场住一宿,安排吃了顿排骨炖豆角。
吃饭的时候闲唠,他说起一件事,说听林场的吴二瞎吹牛逼,在嘉荫靠边境的个叫五家屯的屯子,有古董,好些人家里都发现了一些瓷器和金元宝什么的,发财了。
我当立马就有了点想法——兜里剩200块钱好干啥玩意的啊,不如去嘉荫看看,能不能收点东西,回哈尔滨倒手卖了,说不定能赚一笔。
第二天,我就从饶河坐客车去了双鸭山,双鸭山没有直达嘉荫的车,我先坐火车到了佳木斯,从佳木斯转车到伊春,又从伊春坐客车到了嘉荫。
废了好大劲,才花23块钱雇了个三蹦子,送我去五家屯。

三蹦子,当时有这车就挺牛逼了
五家屯在小兴安岭脚下,也靠着黑龙江,我到的时候是下午,黑龙江已经结冰了,要赶夏天的时候,整片江水离远看都是黑色的,阳光一强江面就晃眼睛。
见过的人才能理解,为什么叫黑龙江。
但现在,江面上盖着一层厚雪,中间被人清理出一片不规则的冰面,几个小逼崽子正在上面滑冰。
三蹦子里面没空调,冻得我嘶哈的,大哥把我放在两排榆树中间,说顺着往里走,就是五家屯。
我下车往里走,大概二百米,进了屯子,和一般的东北农村区别不大,条件好点的住砖房,条件差点点住土房。

东北农村土房
但这村子有点怪,一般来说,东北农村冬天不种地,天太冷出不去门,大家一般都窝家嗑瓜子啥的,但我走了好几家,挨家扒窗户瞅,没人。
屋里啥都有,有的屋子烟囱还冒着白烟,有些人在院里养着狗,看见我嗷嗷叫,但整村的人,就像凭空蒸发了一样。
我听说过一些全村人集体消失的神秘事件,比如清朝道光年间,福建一个一千多人的村落,所有人集体消失。
以及最出名的加拿大爱斯基摩村庄消失事件,1200人的村落忽然一个人没有,消失的人什么东西都没带走,饭菜还摆在桌子上。
最近听说的一次是1987年,陕西的秦岭的一个村庄凭空消失。

村庄消失新闻,不知道真假,我感觉是假的
这些都不知道是真是假,但当时的五家屯,确实一个人也没有。
我当时快吓拉胯了,想跑,但没交通工具,琢磨了一下,还是继续看看,有没有自行车啥的,骑着走。
一直走到村子最东头,都没找着自行车,我血招没有,天也晚了,这时候再往市里走,得冻死在半道,我寻思找一户人家,砸玻璃进去对付一宿,就四处张望了一下。
这时候,发现最东头的土房里,一张脸正贴着窗户,盯着我看,因为嘴在玻璃上哈出白色的雾气,下半张脸看不清。
我被这张脸吓傻逼了,因为我没法分辨这是不是一张人脸——他的左半边脸上,是密密麻麻棕色的鳞片,麻麻赖赖的,看的我都要吐了。
他看见我发现他,从窗口那嘎达消失了,我正准备跑的时候,土房的门开了,他走出了门——是个一米五左右的老太太。
她开口跟我说话,嗓子特别哑:“你找谁啊?”
我说我是哈尔滨来的,听说这儿有古董,来收货的。
老太太咧嘴一笑,说我家就有,你进来看呗。
她左半边脸都是僵硬的鳞片,所以笑起来时,只有半边脸有表情,看着非常诡异。
我不想进去,但确实太TM冷了,脚都冻麻了,就想进屋暖和暖和。
再说了,要真有啥问题,年轻大小伙子,咋地也不可能干不过一个老太太吧。
琢磨了一下,我咔咔就进去了。
你没在农村住过,也没咋住过平房,东北冬天不咋通风,屋里总有股嗖吧的味道,市里面还好一点,农村的很多屋里,味道特别重。
但这老太太屋里的味儿,实在是太难闻了,就像有什么东西臭了,但又有股香味混在里面。
她把我领到里屋,让我上炕,说炕烧的暖和。
我把着炕沿坐下了,她拿起炉子上的水壶,给我倒了碗水,碗上有个豁口,我其实挺渴,但有点嫌埋汰,就没喝。

破炉子上破水壶
老太太也坐到炕上,盯着我看,看得我浑身难受,我把碗放在炕上,说大娘,我问句不该问的哈,那啥玩意,你这脸咋造的?
她说啊,大仙上身之后没送好,,我请了个大仙上身,斗仙,送的时候没送好,没走利索,脸上就开始长鳞片了。
我听她说完这话,浑身一激灵,本来暖和点了,一下又冷了,问她什么是斗仙。
他说就是穿山甲仙。
我说明白了,你是个跳大神的。
她说原来是:“原来是闹堂仙,这两年腿脚不好,二神也死了,不跳了改坐堂仙了。”

上门跳大神的叫闹堂仙,在家不跳神的叫坐堂仙
大侄儿你也知道,你老叔平时最不信这些鬼鬼神神驴马烂什么的,但那次真有点给我震住了。
从我进了五家屯开始,就没啥正常事,人也没了,老太太半边脸长鳞,这玩意搁谁谁不懵啊?
而且人一遇着啥事儿吧,就容易自己脑补,自己吓唬自己。
我当时就越想越吓人——这屯子叫啥?五家屯么!正好在东北,你叫跳大神也好啊所谓出马仙也好,别管叫啥吧,主要就是请五个姓氏的“大仙”。
胡(狐仙)、黄(黄鼠狼)、白(刺猬)、灰(老鼠)、柳(蛇)。
这一下全对上了,当时天还开始黑了,我是走是留,自己都整不明白了。
我当时吓成啥样呢,这么跟你说吧,幸亏咱还算半拉文化人,内心有点道德观念,看那老太太岁太数大了。
要不然当时吓那样了都,真想给她两撇子,看看她是不是真会点魔法啥玩应的。
我估计当时自己声音都有点哆嗦了,问她村里人都哪儿去了。
她说上山了。
我问大冬天上山干啥,她说有人家里老人去世了,大冬天的,土都冻硬了,不好挖,全上山帮忙挖坟去了。
大点的孩子也跟着去了,小点的孩子和老人,都集中在西头的一个屋里呆着,这样能省点柴禾。
我还想问点问题,她打断我,问我不是来收古董么,有个金元宝要不要。
我说行,拿出来看看吧,她去里屋,拿了个三四厘米的小金元宝给我,看着不咋纯,形状也不咋好。
1991年的金价,差不多是现在四分之一吧,再加上她这个纯度不高,我问她多少钱,她说给200就行。

1991年金价,大概是现在的四分之一
我寻思兜里就剩200多块钱,买个这赚不了啥,得看能不能找点更值钱的,就打算等村里人都回来,看看有没有盆盆罐罐啥的。
又过了大概一个来小时吧,天完全黑下来,我看见有几股光源从远处接近,一大堆人打着手电筒,回了五家屯。
我出了跳大神的老太太家,迎了上去。
他们拿着大锅,筛子什么的,牵着几匹驴和马,驴背和马背上都也放了几把铁锹和一些我不认识的工具。
有个带大棉帽子的老头,是村里的支书,问我是干哈的。
我说哈尔滨来的,听说有古董,来收东西的。
他说行,问我晚上住哪儿,用不用给我安排个地方。
我说那太好了,我住一晚,明天收完东西就走,他请我去他家吃饭,白菜炖冻豆腐,蒜茄子,配点小米粥,挺香。
吃饭的时候,支书的儿子把袖子撸了起来,我发现他右胳膊上有几片暗红色的鳞片,和跳大神老太太脸上的一模一样。
那你想,我当时肯定一下就没食欲了,赶紧扒了完饭,让村支书赶紧给我安排住的地方。
他拿了套被褥,把我送到屯子中间,一个弃用了的供销社房子,帮我烧了炉子,说让我对付一宿。

那时候农村都有这种供销社
这村子太邪性了,我虽然又困又累,但不咋敢睡——但凡是个长点心的,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睡觉啊。
我从炉子旁边,拿了烧火的炉钩子放在手边,又躺回了被窝,来回翻身,怎么也睡不着,心里全是事儿。
想着想着,竟然还睡着了。
半夜不知道几点,我让尿憋醒了,想出去放松一下,结果翻个身还没等起,发现有个人正站在窗户边上盯着我看。
我当时就吓醒了,差点没尿裤兜子,但还得装成睡着的样子,窗户边上的人盯了我一会儿就走了。
我眯眼盯着窗户,过了一会儿,窗户边上又出现了另外一张脸。
一直到第二天早上,才很久都没人盯着,我实在憋不住了,膀胱都快爆了,出门尿了泡尿。
结果发现,家家户户都基本已经起了,还有人站在家门口唠嗑抽烟。
他们的对话很奇怪。
一个人问另一个人,说你脸上咋青一块呢?
另一个人回答说,毛尖上撅起来块毛皮,整脸上了,让毛皮给咬了。
然后看见我盯着他俩,俩人都不说话了。
过了一会儿,村支书的儿子拿了俩花卷来,问我睡的怎么样,我瞎客气,说挺好的,这时候屋里蹿出个耗子,我要拿脚踢,他赶紧拦着我,说媳妇儿不能踢,容易遭报应。
我听完他说话,真是浑身不得劲,一分钟不想在这怪屯子多呆了。
赶紧让他挨家挨户带我去看了看,发现村里的瓶瓶罐罐,没有一个像古董的,倒是每家多少都有点金元宝。
我花150收了个小金元宝,打算离开这破地方。
走之前,我寻思跟那半拉脸的老太太告个别,就去了她家,她正把一个铁缸子放在火上加热,里面是一些棕色的液体,正在冒泡。
我问她这是啥,他说是仙药,提神的,问我想不想来点。

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铁罐子
我说还是拉到吧。
出村的时候,村支书他们有准备上山接着挖坟了,我有点奇怪——他们为啥没带任何纸钱类的。
这村子太TM怪了,身上长鳞片,半夜有人站窗户口盯着,管耗子叫老婆,还jb什么让毛皮咬了,咬你妈了个邵子咬,毛皮你奶奶个腿。
但我当时毕竟是个二十啷当岁的年轻人,好奇心重,做事不考虑后果,越想越刺挠。
我从林子里绕过村子,跟着上山人群的脚印,也上了山。
不算旅游景点的话,山里最有人气的地方,其实是坟地。
中国人喜欢把去世的亲人埋在山里,要是能傍个水啥的,就更好了。
咱家祖坟不就在山里么,我记着原来每年初十五,你(徐浪)还跟你爸上山去送灯啥的。
都一样,平时山里没什么人,一逢年过节,就跟TM庙会似的,一堆人带着水果和酒啥的咔咔就来了,在墓碑前叮咣下跪磕头烧纸,贼拉热闹!
但也有些墓碑,从来没人祭拜,毕竟石碑能存在的时间,经常比一个家族更久。
好在还能捡个剩——中国人烧纸都喜欢画个圈,掉在圈外的纸钱,就算给这些孤魂野鬼的了。
现在有小年轻整天说什么出圈出圈的,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,但我感觉出圈不是什么好词,是用来形容没人管的孤魂野鬼的。

冬天上坟去送灯
不扯这些没用的道理了,继续往下讲。
我跟着跟着就感觉不太对劲了——绕山跟着他们的途中,路过了两片坟地,周围就这一个村,他们这祖坟也有点太远了。
绕到了另一边的山脚下,靠着一条冻着的河,这帮人才停下来,我远远的看着他们。
发现他们捡了些树枝子啥的,浇上汽油,在地上面烧起了火,凿冰烧了几大锅水。围着火堆暖和了一会儿,整出了个不知道哪儿弄的柴油发电机,接到一个水泵上,再在水泵上插管子,弄成一个简易的水枪。
几个老爷们把刚才烧的热水往水枪里灌,咔咔呲地面,每呲两三秒就停下,几个人上去赶紧挖几锹,放到一个盆里。
我实在弄不懂这帮人在干啥,远远躲在松林里观察了一会儿,一个摇盆的人大喊一声,出金子了,出金子了。
这下我整明白了——这帮逼在私自开采金矿。

90年代淘金设备
怪不得村里有那么多金元宝,怪不得说祖宗留下很多古董啥的,估计都是自己放出去的谣言,要不然私采金子打出的元宝,解释不清来源。
黑龙江有好几个金矿,除了比较出名的漠河老金沟,还有乌拉嘎金矿,也在嘉荫,离五家屯不远。
这一下咔咔全通了。

黑龙江漠河老金沟,慈禧曾派人在这儿采金
采金人碰上耗子时不能直接说名,也不能伤害,得说时媳妇——因为大家都是掏土挖洞的。
至于被毛皮咬了什么的,应该也是类似的采金黑话,估计五家屯里有人在乌拉嘎金矿干过,教的他们规矩。
这时候山下上来个小孩,走到村支书面前,说了几句话,然后所有采金的人都停下了,开始四处撒么。
我当时心咯噔一下,操蛋了,肯定是有人发现我跟着了。
然后十几个老爷们儿就开始往四处散开,估计是找我呢。
我寻思来时的路肯定有人堵着呢,往山上跑吧,开始鸟悄的爬山,也不知道爬了多长时间,就感觉后面一直有人声。
小兴安岭的山是一座连着一座,我瞎jb爬,也不知道往哪儿去,反正就是逃跑,山道野道都走,大部分地方都有雪,肯定有人能跟着我脚印来。
等到太阳在正中间,差不多中午的时候,我才停下来,确定后边没啥人跟着。
但有一个问题,我迷路了,一月份在山里迷路,和死也差不多,还不如让五家屯的人抓着呢。

下大雪的山上,欢迎你们去东北感受
我只能爬到一个山顶,看着黑龙江的方向,然后向那个方向走,寻思下山沿着江岸走,总能走到有人到地方。
结果下到一半,就发现对面的山上,有一块儿在冒着烟。
我赶紧朝那个方向走,哪怕是抓我的人也认了。
一个小时后,我在荒无人烟的小兴安岭里,发现了一个二层的木屋。
我走过去敲了敲门,一个满脸通红的大胡子拿着一杆不知道是啥的枪指着我,用俄语说Ктоты?
毕竟在俄罗斯呆了半年,我知道他在问我是谁。
我也不会说,但掏出了兜里被废弃的卢布——才废弃没两天,躲在山里的苏联人不一定知道这事儿。
他把钱拿走,回屋拿出一玻璃罐棕色的液体,问我是不是要买这个。
我还能咋整,要呗那咋整,只能点点头,用手势比划问他有没有吃的,他让我进屋,给了我一块大列巴,我就着热水吃了。
等暖和了一会儿,我看了眼手里的玻璃罐,和老太太缸子里加热的仙药挺像。
我怀疑这两伙人有联系,赶紧拿着罐子走了。

当时房间里有些瓶瓶罐罐,不知道干啥的
1月东北白天短,很快天就快黑了,到处都是一片白,每脚下去,都有得有半米深的雪——我完全分不清方向。
雪特别深,跟一直做高抬腿练习似的。
我虽然体力好,但也不想这么浪费,就掰了根树枝,拄着走。
走了几步,插到侧面的雪里使劲时,我右手侧面的位置,也就四米远,半米厚的浮雪被扫掉,漏出了百米深的悬崖,掉下去必死无疑。
我一直以为,悬崖离我很远,但在浮雪的遮掩下,它就在我的身边。
说实话,我已经忘了怎么走下山,怎么找到村落的了,但我总感觉耳边有个声音,在告诉我往哪边走,才能走出这片松林和山,走到有人的地方。
我发了场高烧,得了肺炎,发现我的村民把我送到嘉荫县的医院,那个装满棕色液体的玻璃罐,被我不知丢到哪儿了。
等我清醒过来,到嘉荫县公安局报警,并跟他们一起去到五家屯时,五家屯真的没人了,所有人都跑了,只有那个跳大神的老太太还在,她的半边脸已经烂了。
她用针管从铁罐子里抽出棕色的液体,注射到自己体内,还当着我们面,浇油把房子点了。
在火里,她唱了一段跳大神的歌,有点像二人转的唱腔,不知道为什么,我印象贼TM深,直到今天还记得一段词:
斗内就用高粱米来装满,点上五展油灯煞气冲天,
胡黄二仙就在斗内坐,蛇蟒鹰貂就在斗下边,
清风烟魂闹喧喧,说明咱们胡黄鬼蛇四教全,
这才能够抓着弟子磨香烟,抓的弟马苦连天,
一心秉正要把老仙领,出头露日就在这一天。
我在很多年里,一直没搞清那个棕色的液体,以及五家屯人身上的鳞片,是怎么回事。
直到2002年,俄罗斯开始大范围流行一种名叫“鳄鱼”的毒品,非常廉价,用来代替海洛因的,副作用非常恐怖:使用者的皮肤会像被鳄鱼皮一般呈现鳞片状,肌肉会从体内向外腐烂,最后只剩下光秃秃的骨头。

鳄鱼毒品吸食者手上的鳞片,和老太太脸上的一样
我让俄罗斯的朋友拍了照片寄给我,我确信,那就是俄罗斯人躲在小木屋里制造的棕色液体。
但他怎么和跳大神老太太,包括村支书的儿子联系上,并把毒品卖给他们的,我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了。

注射器里的棕色液体就是鳄鱼毒品
大家好,我是徐浪。
我堂叔徐严的故事,就先讲到这儿吧。
关于那个制毒毒俄罗斯人,我有一些猜测,当年有些俄罗斯人为了制度不被发现,冬天就从冻上的黑龙江过来,在中国边境没人的地方制毒。
之前国家还集中打击过一次。

俄罗斯人跨国制毒新闻图
至于“让毛皮咬了”,确实是淘金行的黑话,意思是被石头砸了。
为了赶更新,我堂叔徐严的这篇故事,有大量细节我没来得及写,只能以后再和大家分享,但我和他聊了聊他当年是如何走出小兴安岭的,是否有神秘的存在,是否改变了他无神论的信仰。
他说还是不信,他认为,人在自己的发展中得到其他实体的支持, 但这些实体不是高级的实体, 天使什么的,而是低级的实体,是动物之类的。
动物崇拜也由此而来。
这话原话不是他说的,是恩格斯说的。
世界从未如此神秘
▬▬▬▬▬●▬▬▬▬▬
We Promise
We Are Original
本文属于虚构,文中图片视频均来自网络,与内容无关。